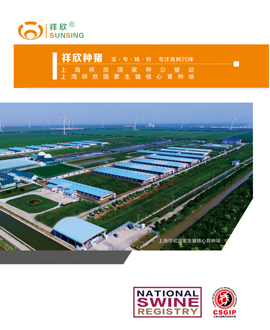追寻猪肉涨价的经济动力
时间:2019-08-17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吴琪
注:本文原载于12年前的《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31期,2007年8月14日
猪肉一向对多数中国人有着特殊意义,畜牧系统的人都知道——“粮猪安天下”。
湘潭市岳塘区板塘乡原农办主任肖建芳感慨:“如果不是城市人吃不到低价肉了,基层农民的生活,很少有人会像这样来关注。”城市人一向认为,粮食和猪肉这些基本生活品,价格越低越能保障人民生活。
这种想法让底层的农民很无奈。
午休时分,湘潭市畜牧水产局总畜牧师吴买生靠在沙发椅上,习惯性嚼着槟榔,“你说怪不怪?去年夏天也是这么热的时候,农民的猪一片片死去,猪肉送人都不敢要”。吴买生和同事们四处求人,让农民把病死猪捞上来按科学方法填埋,处理一只还得付给农民20块钱辛苦费。“那时候猪价最贱,受损的农民哭天喊地。谁能料到,一年后的今天,猪肉如此紧俏,我们要跟在农民屁股后边转,求他们赶紧多养猪呢。”
作为全国五大生猪生产的产业基地,湘潭市下辖5个县市区,其中又以湘潭县和湘乡市的生猪养殖最发达。全市农业人口人均出栏生猪2.8头,养猪占农业产值的58.3%。
这样一个养殖大市,行内人都有直观感觉——今年的猪明显少了。去年3、4月份猪肉价格跌到谷底时候,吴买生就隐隐担心,亏损的农民会大量杀母猪,“种田得有田地在,养猪得有母猪在,淘汰母猪说明行业开始不正常了”。而去年8月一场疫病,让原本低迷的养猪业雪上加霜。这种直观感受也反映在数据上,据湘潭市畜牧水产局统计资料,全市今年1~6月出栏肉猪比去年同期减少13.39%,存栏总量和存栏母猪数分别比去年同期减少12.84%和24.1%。
“出现‘猪荒’是因猪遭了灾,猪遭灾是因为得了病。”在养猪户的逻辑里,疫病成为多数人谈论这场灾难的起点。虽然从生猪养殖到肉价市场的形成链中,疫病只是难以预料的不稳定外来因素,但对于广大分散着的养殖户而言,意外一击往往构成致命一击。
在湘潭,从去年夏天始,染病的猪先是发高烧、皮肤发红、拉肚子,拉到走路都走不稳,很快变为呼吸困难,从发病到死亡,只一星期。在高温高湿的南方地区,母猪开始流产或生死胎。做了20多年畜牧工作的吴买生说:“这次比以往的疾病更可怕,因为它袭击了不同生长周期的猪,染病的母猪、大猪、仔猪接连死亡,生猪生产的结构被改变了。”湘潭农民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上亿元,最严重的一个猪场损失数百万元。当地农民泄气地说,原本指望养猪得到的利益都“喂到猪屁眼里去了”。
与湖南相邻的广东省是湘潭生猪的主要市场,湘潭地处公路交通枢纽,养殖密度大,流动频繁,防控动物疫病难度大,往往是一户发病,一片遭殃。这场最终被确定为“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的疫病,从去年5月首次在江西爆发,很快蔓延至湖南、广东、湖北、安徽、江浙等地。但它在各个省之间传播的路线,却很难说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防疫部门工作人员说,一旦确定某省爆发了疫情,全省养猪卖猪的人就都遭殃了。让行内人印象深刻的是,2005年四川爆发猪链球菌感染,猪肉外调大省四川的养猪业就几乎受到“灭顶之灾”。
在全国猪肉市场大流通的今天,一旦某省或某市疾病信息爆出,等于给自己封锁了所有猪肉出售的路径。
今年5月,去年爆发过的蓝耳病再次侵袭,这次位于湘潭市区边缘的湘潭县响水乡青竹村未能幸免。5月14日,村里的科技副科长莫石奇听说3户村民家里爆发了蓝耳病,马上向村支书卢国良汇报。卢国良带着村干部下去了解,发现病情不止3家,有些农户不愿让人知道自家猪得病,希望还能卖个价钱。5月18日,卢国良将疫情上报到湘潭市畜牧局,第二天市里专家便下村子。经历去年的蓝耳病后,从上至下的应急相当高效,但仍然抵挡不住损失。仅就卢国良所在的月塘组,一共34户农户,29户人家养猪,24户爆发了蓝耳病。全村从5月14日到6月16日,共有2677头猪生病,死亡867头。损失最大的是养猪大户刘福泉和易建辉,刘家死掉了57头猪,易家则病死了116头,“两个大男人在家痛哭”。
记者8月初走访湘潭的好几个村庄,发现养猪户的警惕性极高,他们坚决不让外来人参观猪舍。农民们此时表现的原则性让人有些吃惊,他们对外来细菌的防范也从一个侧面流露了疫病带来的恐慌。“就连自己家的人,也是要消毒后换衣服换鞋子,才能进去的呢!”
猪肉价格的异动,在基层与“猪”打交道的人有更为敏锐的触觉。湘潭市畜牧站站长周炯光说,按照过去20多年猪肉市场的规律,几乎每4年猪价就有一个高峰与低谷的轮回。大家记忆中比较近的年头里,2002年猪价极低,2004年行情到了一个高峰,瘦肉猪的生猪价格能卖到5.2元一斤,农民卖一头猪可以挣200~300元。2006年又到了低谷,仔猪价格更是跌得凶,不论大小一律15元一只,不到2005年高价时的1/10。中国肉类协会副会长陶一山把它归纳为,“农户养猪基本上赚两年亏一年”。今年猪价开始一路向上狂飙,多数养殖户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对去年低价的一个补偿”。
进入6月,行内人感觉到这轮价格反弹得异常。吴买生记得,猪肉市场价每斤涨到八九元的时候,“长沙、湘潭的媒体天天采访,问我的都是同样三个问题:猪肉价格还会不会涨?什么时候回落?生猪的存栏量是多少?”7月初猪肉突破每斤12元,吴买生开始直接接到市领导电话。于是他改变了习惯,每天出门上班第一件事,先上菜市场问问,今天猪肉什么价?刚问完,市领导的电话就追过来了。8月3日这天,湘潭的猪肉卖到每斤15元,长沙卖到16元。吴买生说,“这是在老百姓减少猪肉消费前提下的现有行情,如果大家还像以前那样吃肉,肉价早就突破20元一斤了”。
在肉价引起广泛关注后,一场场追溯猪肉涨价根源的讨论开始了。湘潭市不少机关的工作人员,最近的重点工作是下农村,劝村民们多养猪。村民养猪的意愿,似乎成为人们能不能吃到低价猪肉的原因。
湘潭市板塘乡摇泉村45岁的戴政洪,正在家门口和邻居干着简单的木匠活,高企的猪价看上去和他没有关系,养猪显然不是他今年的重点。戴政洪从1994年开始养猪,因为不愿意出去打工,种菜卖菜成为他的固定收入来源。待到2004年、2005年生猪行情非常看好时,戴政洪的养殖规模也曾达到最高峰,猪舍里有了七八十头猪。但是去年蓝耳病,一些养到100多斤即将出栏的猪病死,加上猪肉价格非常低,他杀了一些猪,血本无归,猪圈里一下子只剩下30多头。多数养殖户如戴政洪一样,行情好的时候马上扩大规模养猪,可是一旦猪多了,价格急跌;看到跌价,农户们又开始杀猪或弃养,猪肉又因为紧缺而涨价。戴政洪有些愁眉苦脸,他对记者说,“我们好像永远赶不上这个趟”。
湘潭县响水乡青竹村的莫石洪则要顺利得多。34岁的他从1997年开始养猪,刚开始只有两头母猪,2002年累积到100多头规模,今年达到500多头,成为青竹村的养猪第一大户。莫石洪的理论很简单,在经历1998年、2002年两个低谷期后,他发现养猪的行情即使再不好,“当年只有一两个月亏本,挺过去就好了”。所以莫石洪一直没有缩减规模,猪越养越好。
在经济学家的眼里,莫石洪显然比戴政洪高明得多。戴政洪看到的总是眼下的猪价,而忽略了生猪养殖6个月的生长期,没看到价格变化的规律。当然,莫石洪家的经济基础更好,对风险的抵御能力也更强。当养猪户每一年亏损或赢利的时候,他们的意愿决定了生猪存栏数量的变化,而他们的意愿又根据什么呢?有的农户看看隔壁邻居的猪圈,决定今年自己的投入。有些根据自己当年的经济状况决定,有些也开始对市场规律做预测。光大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对这种预期做分析,农户在观察到价格变动后,形成了通货膨胀预期,这导致农户存粮(以及存栏生猪)意愿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影响了粮食和猪肉价格。
在高善文看来,猪肉涨价并不是一轮涨价的启动因素,反而是经济制造部门和服务部门的价格变化,决定了粮食和猪肉等农产品的价格走势。这种传播渠道包括饲料、化肥在内的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变化引发种粮和养猪成本变动,影响了粮食和猪肉的价格。
高善文认为,2004年底到2006年初,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工业增长率开始下降,带动中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不断回落。由于中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在此期间的回落,包括粮食、猪肉在内的食品类价格指数也开始同步下降。猪肉价格下降挫伤了农户养猪的积极性,生猪的存栏数出现下降。2006年初全球经济体的工业增长率开始回升,一个季度后,中国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止跌回升,大约与此同步,猪肉和粮食等的价格也开始上升。伴随猪肉价格的上升,生猪存栏数问题开始逐步暴露,并在今年5月引起了广泛注意。
但是由于中国缺乏指数化债券等金融工具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及其变化是无法直接观察的。在自发而散乱的市场关系中,养猪农民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变得难以掌握。上至国家相关部门,下到养殖户,因而很难对市场做准确预期。猪肉行业仍然在几年循环一次高峰低谷的状况中徘徊,只是这次肉价的反弹,在综合多种因素后,变得异常。
1999~2000年湘潭市畜牧水产局在响水乡青竹村办生猪产业联系点,当时作为副村长的卢国良引进项目,遭遇2001年生猪大降价,“养一头猪亏50~80元,好多人来我家又哭又闹”。卢国良冥思苦想找原因,1999~2000年猪肉行情不错,农民每头猪能赚80~100元,等到农民因猪价低而亏损时,那些收购猪肉的中间贩子大肆压价压秤,仍然能赚不少钱。卢国良于是决定和村民们撇开中间商贩。2002年,他向当时的湘潭市畜牧水产局局长和农办主任联系,通过他们直接找收购和加工生猪的大公司,建立了“公司+协会+农户”的“青竹模式”。
196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到上海青浦农村考察,写下了著名的《青浦农村调查》。在当时大跃进的背景下,他考察私养猪和公养猪的问题,发现私养猪比公养猪吃得饱、吃得好。当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如今早已克服,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20多年后,完全放开的最底层养猪户意识到了另一种风险,开始自发寻求某种调控力量来解决困境。
现在的青竹村是一个由412户村民组成的行政单位,与周围村子比没有任何地理上的优势,耕地面积与种植小水果的面积相当,在1600~1800亩的范围内,池塘养鱼是部分村民的副业。从2002年起成立了生猪产业发展协会后,青竹村将原本小规模散养的农户集中起来,统一购销、统一引种、统一防疫、统一饲料。当把这个普通的村子作为一个调查对象时,它的养猪户结构在这几年发生了有趣的变化。
从2004年起,卢国良和村干部开始调研统计村子里的各种数据,“当时主要是想了解养猪的利益和村民外出务工的状况”。2004年全村412户里边有378户养猪,而经过接下来两年行情波动,如今只有228户养猪。有意思的发现是,3年时间里被淘汰的150户,养猪规模全部在8~50头之间,规模最小的2~8头的养殖户存活了下来,50头以上的越来越壮大。规模效应在青竹村不知不觉显现出来。
养2~8头猪的小户人家,并不需要专门的劳动力来喂猪,家里的剩饭剩菜和菜地里的青菜可以当食物,节省了不少饲料成本。而且青竹村沼气入户率88%,沼气池需要猪粪作为能源循环。对于8头猪以下的村民来说,他们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每年有几千元的卖猪赢利。
对于50头以上的养殖户而言,规模效应为他们节省了成本。按照青竹村算的一笔账,饲料价格、感染疫病的风险和劳动力价格上涨,成为农民养猪必须考虑的三大成本。饲料成本的增加在近几年来尤为明显。从更广泛的视野,全球商品从2002年进入牛市,几乎所有的资源型商品都进入快速上升。铁矿石、铜价、镍价、石油、大豆、玉米都在持续涨价,累计上涨的幅度超过100%。工业资源和农作物资源价格上涨逐渐传播到终端消费品中,从2006年初开始粮油价格普遍上涨。这种链条也早已传导到村子里的养殖户。以一头120公斤的猪为例,2004年饲料成本为580元,2007年上涨到958元。于是养一头120公斤的猪,所需饲料成本在3年内涨了378元。那些养殖规模50头以上的农户,可以自己配置优质低价的全价料,并且猪舍等硬件投资已经算入成本,消毒防疫也能节省耗费。
不过,养50头猪在卢国良这样有16年养殖经验的人看来,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事。因为养50头或200头猪,所需都只是一个劳动力,也就是说,所花费劳动力成本是一样的。这两年农村劳动力的价格上涨非常显著,2004年一个农民工一天的价格为25元,2007年涨到60元一天。卢国良算了这样一笔账,养200头猪的人家,一年能出栏400头猪(猪的出栏周期为五六个月),如果每头猪给劳动力30元的工钱,那么这个劳动力一年能挣到1.2万元。可是对于养50头猪的人,一年出栏100头,劳动力只能赚到3000元。那么养猪的帮工显然愿意去给200头的大户打工,而不愿意让自己的劳动力闲置。当养猪规模达不到200头的时候,一个劳动力显得过剩,没有充分利用它的价值。
从2005年开始,劳动力价格上扬对于掌握熟练技术的农民工而言,增幅特别显著。这部分脱离农村十几年、已经完全靠娴熟的非农业技艺生活的人,虽然在户籍上仍然是农村人口,但在生产方式上已经彻底脱离土地了。
李文斌的父亲李森林一直住在湘潭县的青竹村,但也能明显感觉到这种变化。比较起来,29岁的小儿子李剑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家务农,一亩梨树一年下来收益才200元,好在今年猪肉行情不错,家里养的90多头猪,能够收入7万多元。
打工和种田的收益差别一直在增大,对于青竹村村民或任何一个农业人口来说,都存在一个比较效益:是外出打工还是在家种田、养猪?劳动力价格与农业收入的比较,是农民留在田地或是进城打工的决定因素。2002年,农民工平均一天的工钱是20元,2006年上半年平均一天30元,这4年间涨幅并不大。但是2006年下半年涨到40元一天,待到2007年春节以后,暴涨到60元。在湘潭,每天请一个临时的农民工,除了60元工钱,还要包两顿饭,给一包烟和一包槟榔,雇主一天给每人的花费近80元。
而如果选择种田,农业生产的成本在不断提高,比如种田必须的碳氨和尿素,从2004年到2007年,每百斤分别上涨了7元和15元。每亩田地的耕种费,由2004年的80元涨到如今的150元。增长最高的是人工,开耕种机的人一天的工资,由每天30元涨到80元,开收割机的工资,由每亩65元涨到85元。
因此多数农民更愿意外出打工,比起种地养猪等农活,打工没有风险。据统计,整个响水乡抛荒的土地上千亩,至少在1/40以上,而常德农村抛荒土地达到1/10。2006年夏天,中组部、农业部组织专家在北戴河开暑期休假座谈会时,特意邀请了开创“青竹养猪模式”的卢国良参加。卢国良给大家算了一笔账,讲述农民今年为何频频抛荒。
卢国良在几年详细统计村民家庭状况后,得到这样一套极有启发性的计算方式。以青竹村的实际情况,一年种早、晚两季稻子。一年下来,每亩地的生产成本包括种子、农药、化肥、雇佣耕种机、收割机费用等共计610元。一年每亩地需要30个劳动工,以现在农民打工每天收入60元来算,一年每亩地的人工成本为30×60=1800元。那么综合起来,一亩地需要生产成本610元加人工成本1800元,得出2410元的成本。以收益看,一亩地一年产稻900公斤,能卖出1350元。于是农民种每亩地的亏损为2410元与1350元的差额,即1060元。
在农民的种地成本中,卢国良以每亩1800元作为人工成本相当特别。虽然是在计算土地方面的收益,但是卢国良以农民打工的价格来衡量在土地上付出的劳动力价格。在2410元的总成本中,1800元劳动力成本占到近3/4。也就是说,农民如果选择种地,他的劳动力价值得不到相应的承认。
养猪、种果树或外出打工,农民也通过比较效益得出各家的结论。在养猪大村青竹村,养猪是最主要的农业收入。全村通过调查发现,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收入与养猪收入两项是全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而劳动力在城乡间的往来状况,与养猪收益成反向流动。
2002年和2006年猪肉行情低迷时候,形成了青竹村两个外出打工的高峰期。青竹村全村1557人,16~60周岁的男女劳动力有815人。其中,学校毕业到50岁以内的中青年劳力385人,卢国良以这385名中壮年劳动力作为调查对象。他发现,这部分人当中有25%的人是30岁以内有一定学历的,从中学或中专、大专毕业后,基本到沿海城市去打工,从事电子、通讯等行业里的技术工人。对于年轻人来说,主要是“价值观”使他们不愿继续留在农村,希望远离养猪种菜等农活。他们一年收入在1万~1.5万元之间,平均每年寄给家里5000~8000元。可见他们在城市中,生活并不富裕,属中下阶层。
在从学校毕业到50岁以内的中青年劳力385人中,有50%的人属于打工和务农兼顾的人群。他们在30岁到50岁之间,没有什么学历,已经在农村拖家带口,习惯于农业生产。为了使日子过得更好,他们基本选择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打临工。2003年,离村子仅仅两三公里,新建九华工业园区,需要大量劳动力。附近村庄30~50岁之间干建筑和装修的农民,白天在工地打工,晚上回家也可以兼顾一些农活,日子比较稳定。每年在外打工的收入在1万~1.1万元之间。
在城市边缘的九华工业园做更低级的收杂料、做木工的,则是村子里50岁以上的劳力,占到外出总劳力的10%。他们全职打工,并不兼顾农活。每年收入在1万~1.5万元之间。另外占到15%的外出劳力为女性打工,基本上在附近城市的纺织厂、槟榔加工厂工作。这些30岁到50岁之间的女性,并不兼顾家里的农活,每年务工收入在8000元左右。
2004年猪肉行情的高峰时期,青竹村外出打工人数最少,只有不到200人,仅为平时的一半。在养猪容易挣钱的年头,多数人选择回家干活而不去城市,只有30岁以下彻底希望抛弃农村的打工者才不会回家。
记者发现,近几年养猪这样的农副产品规模效应出现后,农村人口也出现分化。一部分靠养猪致富的大户,从养殖业里得到的收益已经远远大于进城打工,他们成为安心留在土地上的农业人口。以青竹村的莫石洪为例,500多头猪能为他一年带来30多万元的效益,四口之家无需外出打工来补贴。而其他30岁以下的年轻人,如果没有成为成功的养猪或种植户,宁愿一直在城市漂泊下去,等待着像李文斌一样,成为娴熟的城市工人,得到不错的回报。不少经济学家正在预测,随着中国工业化加速,“刘易斯拐点”是不是即将到来。虽然目前并没有确切的数据统计,但是随着实际上的农业人口减少,农业部门大量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判断,在基层的养猪大村也得到体现。
湘潭市岳塘区板塘乡的摇泉村已经被纳入了城市边缘,随着城市扩展,村子里水泥路边的房子紧凑地挤在一起,村民们人均只有两分耕地了。养猪在摇泉村占到农业收入60%~70%,村子紧挨着中央储备粮湘潭直属库,可以得到低价的玉米、麦麸等猪饲料。但是近几年工业企业发展非常迅速,37岁的肖建芳曾任板塘乡农办主任,现在是板塘乡政府企业办的工作人员,他掰指一算,板塘乡已有5个纺织厂、2家建材企业、7家砖厂,另加好几个炉具厂等。从2005年开始,肖建芳就明显感觉到这些企业的重劳动力特别缺乏,“农民的生活在提高,打工技能越来越好,很少人愿意干重体力活”。而不断扩大的企业生产线急需大批工人,致使数年前汹涌的民工潮,近两年变为短缺的民工荒了。湘潭钢铁厂前阵子到附近农村招工,每月1000多元的待遇,仍然招不够人。
湘潭处在丘陵地带,种田主要靠人力,很难大面积实行机械化。村子在不断变为城市,田地变成了水泥路,靠农业为生的人逐渐减少。
虽然湘潭的生猪产业化在全国已经领先,但所谓的产业化,与发达国家的方式相比,更多的还是“大散养”的格局。农民依然以一家一户的庭院式圈养为主,只是多数规模比以前大。肖建芳说,摇泉村2004年曾经设想过在村子里开辟一大片空地,真正把养猪业集中起来。但是城市化步伐太快,村子里的地也被纳入城市规划。湘潭市现在有各类养殖协会156个,一个成功的协会能够吸引几百家养猪户,在协会内部信息畅通。猪肉的产业链包括“饲料供应——良种供应——生猪养殖——生猪屠宰——猪肉分销——猪肉深加工”等环节,只是农户庭院式散户养殖依然是“小农经济”的传统。肖建芳有些感慨:“如果不是城市人吃不到低价肉了,基层农民的生活,很少有人会像这样来关注。”
经常到农村做防疫的湘潭市畜牧水产局总畜牧师吴买生感受到,多数农户渐渐对价格的波动有了自己的判断,即使今年行情再好,有些农民也只是摇摇头,“万一都开始养猪,过两年岂不是又跌得很惨?”在玉米、大豆都进入全球化、资本化的今天,小户式的生猪生产方式无疑受到严峻的挑战。去年“猪贱伤农”的经历,使吴买生和养猪户对今年的高行情也产生担心,“猪价并不是越高越好,今年是刚好赶上猪价自身的波动和去年疫情影响,高得不正常”。但是城市人口却一向认为,粮食和猪肉这些基本生活品,价格越低越能保障人民生活,这种想法让底层的农民很无奈。吴买生和卢国良在算账后都觉得,猪肉卖到10元一斤的行情,是目前“既能让农民获利,也能让城市人接受的价格,这种价格才能长期稳定”。
王伟筠是大连商品交易所信息部的副部长,自从最近猪肉行情飙升,大商所(大连商品交易所)推出生猪期货的设想就引起广泛关注。王伟筠说,其实大商所从2001年就开始对生猪期货的推出进行调研,在1995年粮油猛涨时候,很多人对刚刚推出的期货有误解,认为期货市场使物价进一步哄抬。“这就好像一个人自己长得难看,却怪罪于照出他面容的镜子。”现在一般人都认识到期货市场稳定价格体系的作用,稻谷、生猪与基本生活最接近的品种这些有可能进入期货市场,“期货市场将各种相关因素都装进了市场里边,市场加工出来的价格更全面,有预期性,它比一个单独养猪户的判断要可靠得多”。
当猪肉价格涨到十五六元一斤的时候,就在湘潭市畜牧水产局的新办公大楼里,任何与“猪”有关的人,都在团团转。8月初,湘潭市下属各区县的畜牧水产局负责人、兽医站的人都聚集起来开会,主管业务的副局长则在省里头接受最新指示。作为全国生猪主产地之一的湘潭,按照市畜牧站站长周炯光的说法,这里人均猪肉产量全国第一,但从未感觉“像今天这样受到重视”。农业部下派的工作组7月23、24、25日连续三天来到湘潭调查,每个县抽查30个典型养殖户,“光是每一户要填的表格,就有30多个”。7月26日,一份“赴湖南生猪生产督导组”的《湘潭市发展生猪生产的调查报告》就出来了。
与湖南类似,农业部7月底下派的20个工作组紧急来到全国各生猪主产区。7月26日,在长沙的湖南宾馆,农业部副部级总经济师和科技司司长带队的湖南工作组将湘潭、长沙、娄底三地的情况聚集在一起汇报。湖南省畜牧局水产局罗局长引用了两句话说明当前的形势,“无肉使人瘦”、“不可三日食无肉”,猪肉一向对多数中国人有着特殊意义。周炯光说,畜牧系统的人都知道一句话——“粮猪安天下”,老百姓吃不到猪肉与吃不到粮食一样难受。但是国家对粮食供应一直有特殊的保护政策,生猪市场在上世纪80年代完全放开后,除了中央储备肉基地等保障措施,基层养猪户的利益并没有纳入过国家的保障体系。
虽然形势紧张,拿着手里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吴买生和同事们都相当欣喜,因为文件“实在、特别容易操作”,有些措施正是7月底农业部调查后的结果。新措施让农民兴奋,“国家按每头50元的补贴标准,对饲养能繁殖母猪的养殖户(场)给予补贴”、“国家建立能繁母猪保险制度”、“国庆两节猪肉供应,猪肉主销区省、直辖市及沿海大中城市要将地方储备充实到不低于当地居民7天消费量”。吴买生与同事这几天正忙着到村子里统计母猪数量和人工授精的情况。只是他还有一点担心:“文件非常好,却没有说明这些政策执行到什么时候?”吴买生希望应急措施成为长期措施,“不然过两年猪价又像坐电梯一样往下掉,结果还是会猪贱伤农啊。”
责任编辑:乔春玲
猪肉一向对多数中国人有着特殊意义,畜牧系统的人都知道——“粮猪安天下”。
湘潭市岳塘区板塘乡原农办主任肖建芳感慨:“如果不是城市人吃不到低价肉了,基层农民的生活,很少有人会像这样来关注。”城市人一向认为,粮食和猪肉这些基本生活品,价格越低越能保障人民生活。
这种想法让底层的农民很无奈。
“引子”:疫病
8月3日,湖南省版图中部偏东的湘江流域,距长沙仅40多公里,全国“养猪百强大市”湘潭气氛紧张。气温近40摄氏度,长沙正遭遇50年一遇的大旱,这场干旱也影响到湘潭。长江今年的最大洪峰此刻正通过武汉,而在湘潭,一场抵抗“猪荒”的战役,也如同对洪水的抗争,紧张忙碌。午休时分,湘潭市畜牧水产局总畜牧师吴买生靠在沙发椅上,习惯性嚼着槟榔,“你说怪不怪?去年夏天也是这么热的时候,农民的猪一片片死去,猪肉送人都不敢要”。吴买生和同事们四处求人,让农民把病死猪捞上来按科学方法填埋,处理一只还得付给农民20块钱辛苦费。“那时候猪价最贱,受损的农民哭天喊地。谁能料到,一年后的今天,猪肉如此紧俏,我们要跟在农民屁股后边转,求他们赶紧多养猪呢。”
作为全国五大生猪生产的产业基地,湘潭市下辖5个县市区,其中又以湘潭县和湘乡市的生猪养殖最发达。全市农业人口人均出栏生猪2.8头,养猪占农业产值的58.3%。
这样一个养殖大市,行内人都有直观感觉——今年的猪明显少了。去年3、4月份猪肉价格跌到谷底时候,吴买生就隐隐担心,亏损的农民会大量杀母猪,“种田得有田地在,养猪得有母猪在,淘汰母猪说明行业开始不正常了”。而去年8月一场疫病,让原本低迷的养猪业雪上加霜。这种直观感受也反映在数据上,据湘潭市畜牧水产局统计资料,全市今年1~6月出栏肉猪比去年同期减少13.39%,存栏总量和存栏母猪数分别比去年同期减少12.84%和24.1%。
“出现‘猪荒’是因猪遭了灾,猪遭灾是因为得了病。”在养猪户的逻辑里,疫病成为多数人谈论这场灾难的起点。虽然从生猪养殖到肉价市场的形成链中,疫病只是难以预料的不稳定外来因素,但对于广大分散着的养殖户而言,意外一击往往构成致命一击。
在湘潭,从去年夏天始,染病的猪先是发高烧、皮肤发红、拉肚子,拉到走路都走不稳,很快变为呼吸困难,从发病到死亡,只一星期。在高温高湿的南方地区,母猪开始流产或生死胎。做了20多年畜牧工作的吴买生说:“这次比以往的疾病更可怕,因为它袭击了不同生长周期的猪,染病的母猪、大猪、仔猪接连死亡,生猪生产的结构被改变了。”湘潭农民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上亿元,最严重的一个猪场损失数百万元。当地农民泄气地说,原本指望养猪得到的利益都“喂到猪屁眼里去了”。
与湖南相邻的广东省是湘潭生猪的主要市场,湘潭地处公路交通枢纽,养殖密度大,流动频繁,防控动物疫病难度大,往往是一户发病,一片遭殃。这场最终被确定为“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的疫病,从去年5月首次在江西爆发,很快蔓延至湖南、广东、湖北、安徽、江浙等地。但它在各个省之间传播的路线,却很难说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防疫部门工作人员说,一旦确定某省爆发了疫情,全省养猪卖猪的人就都遭殃了。让行内人印象深刻的是,2005年四川爆发猪链球菌感染,猪肉外调大省四川的养猪业就几乎受到“灭顶之灾”。
在全国猪肉市场大流通的今天,一旦某省或某市疾病信息爆出,等于给自己封锁了所有猪肉出售的路径。
今年5月,去年爆发过的蓝耳病再次侵袭,这次位于湘潭市区边缘的湘潭县响水乡青竹村未能幸免。5月14日,村里的科技副科长莫石奇听说3户村民家里爆发了蓝耳病,马上向村支书卢国良汇报。卢国良带着村干部下去了解,发现病情不止3家,有些农户不愿让人知道自家猪得病,希望还能卖个价钱。5月18日,卢国良将疫情上报到湘潭市畜牧局,第二天市里专家便下村子。经历去年的蓝耳病后,从上至下的应急相当高效,但仍然抵挡不住损失。仅就卢国良所在的月塘组,一共34户农户,29户人家养猪,24户爆发了蓝耳病。全村从5月14日到6月16日,共有2677头猪生病,死亡867头。损失最大的是养猪大户刘福泉和易建辉,刘家死掉了57头猪,易家则病死了116头,“两个大男人在家痛哭”。
记者8月初走访湘潭的好几个村庄,发现养猪户的警惕性极高,他们坚决不让外来人参观猪舍。农民们此时表现的原则性让人有些吃惊,他们对外来细菌的防范也从一个侧面流露了疫病带来的恐慌。“就连自己家的人,也是要消毒后换衣服换鞋子,才能进去的呢!”
猪价模糊的传导链
疫病流行,给了人们一种说得过去的解释,就像天气不好会导致粮食歉收一样,谁能杜绝坏天气呢?连续两年的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流行,导致生猪存栏数下降,成为猪肉涨价的一个直观原因。但从更深层的经济分析,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天气、瘟疫等因素虽然也影响粮食和猪肉价格,但这些供给方面的扰动可能是一次性的,对价格趋势的影响更多属于随机的扰动项。猪肉价格的变动是怎样传递的,在持续上扬的价格体系中,谁在推动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呢?猪肉价格的异动,在基层与“猪”打交道的人有更为敏锐的触觉。湘潭市畜牧站站长周炯光说,按照过去20多年猪肉市场的规律,几乎每4年猪价就有一个高峰与低谷的轮回。大家记忆中比较近的年头里,2002年猪价极低,2004年行情到了一个高峰,瘦肉猪的生猪价格能卖到5.2元一斤,农民卖一头猪可以挣200~300元。2006年又到了低谷,仔猪价格更是跌得凶,不论大小一律15元一只,不到2005年高价时的1/10。中国肉类协会副会长陶一山把它归纳为,“农户养猪基本上赚两年亏一年”。今年猪价开始一路向上狂飙,多数养殖户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对去年低价的一个补偿”。
进入6月,行内人感觉到这轮价格反弹得异常。吴买生记得,猪肉市场价每斤涨到八九元的时候,“长沙、湘潭的媒体天天采访,问我的都是同样三个问题:猪肉价格还会不会涨?什么时候回落?生猪的存栏量是多少?”7月初猪肉突破每斤12元,吴买生开始直接接到市领导电话。于是他改变了习惯,每天出门上班第一件事,先上菜市场问问,今天猪肉什么价?刚问完,市领导的电话就追过来了。8月3日这天,湘潭的猪肉卖到每斤15元,长沙卖到16元。吴买生说,“这是在老百姓减少猪肉消费前提下的现有行情,如果大家还像以前那样吃肉,肉价早就突破20元一斤了”。
在肉价引起广泛关注后,一场场追溯猪肉涨价根源的讨论开始了。湘潭市不少机关的工作人员,最近的重点工作是下农村,劝村民们多养猪。村民养猪的意愿,似乎成为人们能不能吃到低价猪肉的原因。
湘潭市板塘乡摇泉村45岁的戴政洪,正在家门口和邻居干着简单的木匠活,高企的猪价看上去和他没有关系,养猪显然不是他今年的重点。戴政洪从1994年开始养猪,因为不愿意出去打工,种菜卖菜成为他的固定收入来源。待到2004年、2005年生猪行情非常看好时,戴政洪的养殖规模也曾达到最高峰,猪舍里有了七八十头猪。但是去年蓝耳病,一些养到100多斤即将出栏的猪病死,加上猪肉价格非常低,他杀了一些猪,血本无归,猪圈里一下子只剩下30多头。多数养殖户如戴政洪一样,行情好的时候马上扩大规模养猪,可是一旦猪多了,价格急跌;看到跌价,农户们又开始杀猪或弃养,猪肉又因为紧缺而涨价。戴政洪有些愁眉苦脸,他对记者说,“我们好像永远赶不上这个趟”。
湘潭县响水乡青竹村的莫石洪则要顺利得多。34岁的他从1997年开始养猪,刚开始只有两头母猪,2002年累积到100多头规模,今年达到500多头,成为青竹村的养猪第一大户。莫石洪的理论很简单,在经历1998年、2002年两个低谷期后,他发现养猪的行情即使再不好,“当年只有一两个月亏本,挺过去就好了”。所以莫石洪一直没有缩减规模,猪越养越好。
在经济学家的眼里,莫石洪显然比戴政洪高明得多。戴政洪看到的总是眼下的猪价,而忽略了生猪养殖6个月的生长期,没看到价格变化的规律。当然,莫石洪家的经济基础更好,对风险的抵御能力也更强。当养猪户每一年亏损或赢利的时候,他们的意愿决定了生猪存栏数量的变化,而他们的意愿又根据什么呢?有的农户看看隔壁邻居的猪圈,决定今年自己的投入。有些根据自己当年的经济状况决定,有些也开始对市场规律做预测。光大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对这种预期做分析,农户在观察到价格变动后,形成了通货膨胀预期,这导致农户存粮(以及存栏生猪)意愿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影响了粮食和猪肉价格。
在高善文看来,猪肉涨价并不是一轮涨价的启动因素,反而是经济制造部门和服务部门的价格变化,决定了粮食和猪肉等农产品的价格走势。这种传播渠道包括饲料、化肥在内的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变化引发种粮和养猪成本变动,影响了粮食和猪肉的价格。
高善文认为,2004年底到2006年初,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工业增长率开始下降,带动中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不断回落。由于中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在此期间的回落,包括粮食、猪肉在内的食品类价格指数也开始同步下降。猪肉价格下降挫伤了农户养猪的积极性,生猪的存栏数出现下降。2006年初全球经济体的工业增长率开始回升,一个季度后,中国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止跌回升,大约与此同步,猪肉和粮食等的价格也开始上升。伴随猪肉价格的上升,生猪存栏数问题开始逐步暴露,并在今年5月引起了广泛注意。
但是由于中国缺乏指数化债券等金融工具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及其变化是无法直接观察的。在自发而散乱的市场关系中,养猪农民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变得难以掌握。上至国家相关部门,下到养殖户,因而很难对市场做准确预期。猪肉行业仍然在几年循环一次高峰低谷的状况中徘徊,只是这次肉价的反弹,在综合多种因素后,变得异常。
青竹村养猪的成本核算
具体到每个单独的农户,决定每一年养猪投入的,是自家的一本小经济账。卢国良是湖南一个普通村子的村支书,却因为对农村新经济模式的尝试和研究名声不小。记者见到他时,卢国良正在解决村里的抗旱问题,从湘潭市东北郊沿着仅有的一条水泥路走进深处的村庄,两边青油油的水稻刚插进不久。但是今年的大旱使晚稻只插了往年的30%,不少田地干旱得种不下稻子。1999~2000年湘潭市畜牧水产局在响水乡青竹村办生猪产业联系点,当时作为副村长的卢国良引进项目,遭遇2001年生猪大降价,“养一头猪亏50~80元,好多人来我家又哭又闹”。卢国良冥思苦想找原因,1999~2000年猪肉行情不错,农民每头猪能赚80~100元,等到农民因猪价低而亏损时,那些收购猪肉的中间贩子大肆压价压秤,仍然能赚不少钱。卢国良于是决定和村民们撇开中间商贩。2002年,他向当时的湘潭市畜牧水产局局长和农办主任联系,通过他们直接找收购和加工生猪的大公司,建立了“公司+协会+农户”的“青竹模式”。
196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到上海青浦农村考察,写下了著名的《青浦农村调查》。在当时大跃进的背景下,他考察私养猪和公养猪的问题,发现私养猪比公养猪吃得饱、吃得好。当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如今早已克服,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20多年后,完全放开的最底层养猪户意识到了另一种风险,开始自发寻求某种调控力量来解决困境。
现在的青竹村是一个由412户村民组成的行政单位,与周围村子比没有任何地理上的优势,耕地面积与种植小水果的面积相当,在1600~1800亩的范围内,池塘养鱼是部分村民的副业。从2002年起成立了生猪产业发展协会后,青竹村将原本小规模散养的农户集中起来,统一购销、统一引种、统一防疫、统一饲料。当把这个普通的村子作为一个调查对象时,它的养猪户结构在这几年发生了有趣的变化。
从2004年起,卢国良和村干部开始调研统计村子里的各种数据,“当时主要是想了解养猪的利益和村民外出务工的状况”。2004年全村412户里边有378户养猪,而经过接下来两年行情波动,如今只有228户养猪。有意思的发现是,3年时间里被淘汰的150户,养猪规模全部在8~50头之间,规模最小的2~8头的养殖户存活了下来,50头以上的越来越壮大。规模效应在青竹村不知不觉显现出来。
养2~8头猪的小户人家,并不需要专门的劳动力来喂猪,家里的剩饭剩菜和菜地里的青菜可以当食物,节省了不少饲料成本。而且青竹村沼气入户率88%,沼气池需要猪粪作为能源循环。对于8头猪以下的村民来说,他们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每年有几千元的卖猪赢利。
对于50头以上的养殖户而言,规模效应为他们节省了成本。按照青竹村算的一笔账,饲料价格、感染疫病的风险和劳动力价格上涨,成为农民养猪必须考虑的三大成本。饲料成本的增加在近几年来尤为明显。从更广泛的视野,全球商品从2002年进入牛市,几乎所有的资源型商品都进入快速上升。铁矿石、铜价、镍价、石油、大豆、玉米都在持续涨价,累计上涨的幅度超过100%。工业资源和农作物资源价格上涨逐渐传播到终端消费品中,从2006年初开始粮油价格普遍上涨。这种链条也早已传导到村子里的养殖户。以一头120公斤的猪为例,2004年饲料成本为580元,2007年上涨到958元。于是养一头120公斤的猪,所需饲料成本在3年内涨了378元。那些养殖规模50头以上的农户,可以自己配置优质低价的全价料,并且猪舍等硬件投资已经算入成本,消毒防疫也能节省耗费。
不过,养50头猪在卢国良这样有16年养殖经验的人看来,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事。因为养50头或200头猪,所需都只是一个劳动力,也就是说,所花费劳动力成本是一样的。这两年农村劳动力的价格上涨非常显著,2004年一个农民工一天的价格为25元,2007年涨到60元一天。卢国良算了这样一笔账,养200头猪的人家,一年能出栏400头猪(猪的出栏周期为五六个月),如果每头猪给劳动力30元的工钱,那么这个劳动力一年能挣到1.2万元。可是对于养50头猪的人,一年出栏100头,劳动力只能赚到3000元。那么养猪的帮工显然愿意去给200头的大户打工,而不愿意让自己的劳动力闲置。当养猪规模达不到200头的时候,一个劳动力显得过剩,没有充分利用它的价值。
劳动力价格上升: 农民比较效益的核心因素
30岁的李文斌在长沙打工13年,他的生活如今看上去和一个城市的白领没有多大区别了。月薪5000元,长沙某钢结构公司的项目经理,去年才结婚的他已经不像村子里的伙伴,早早就拖家带口。1995年17岁的李文斌高中毕业离开青竹村时,从未学过建筑知识的他只能在工地当学徒,每月300元收入,1998年增加到600元,2000年月入1000元。从2005年开始,技术越来越熟练的他每月能有1600元的收入,而随着李文斌今年的一次跳槽,由于已经能独立承担项目,月薪达到5000,在长沙已属中高收入。从2005年开始,劳动力价格上扬对于掌握熟练技术的农民工而言,增幅特别显著。这部分脱离农村十几年、已经完全靠娴熟的非农业技艺生活的人,虽然在户籍上仍然是农村人口,但在生产方式上已经彻底脱离土地了。
李文斌的父亲李森林一直住在湘潭县的青竹村,但也能明显感觉到这种变化。比较起来,29岁的小儿子李剑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家务农,一亩梨树一年下来收益才200元,好在今年猪肉行情不错,家里养的90多头猪,能够收入7万多元。
打工和种田的收益差别一直在增大,对于青竹村村民或任何一个农业人口来说,都存在一个比较效益:是外出打工还是在家种田、养猪?劳动力价格与农业收入的比较,是农民留在田地或是进城打工的决定因素。2002年,农民工平均一天的工钱是20元,2006年上半年平均一天30元,这4年间涨幅并不大。但是2006年下半年涨到40元一天,待到2007年春节以后,暴涨到60元。在湘潭,每天请一个临时的农民工,除了60元工钱,还要包两顿饭,给一包烟和一包槟榔,雇主一天给每人的花费近80元。
而如果选择种田,农业生产的成本在不断提高,比如种田必须的碳氨和尿素,从2004年到2007年,每百斤分别上涨了7元和15元。每亩田地的耕种费,由2004年的80元涨到如今的150元。增长最高的是人工,开耕种机的人一天的工资,由每天30元涨到80元,开收割机的工资,由每亩65元涨到85元。
因此多数农民更愿意外出打工,比起种地养猪等农活,打工没有风险。据统计,整个响水乡抛荒的土地上千亩,至少在1/40以上,而常德农村抛荒土地达到1/10。2006年夏天,中组部、农业部组织专家在北戴河开暑期休假座谈会时,特意邀请了开创“青竹养猪模式”的卢国良参加。卢国良给大家算了一笔账,讲述农民今年为何频频抛荒。
卢国良在几年详细统计村民家庭状况后,得到这样一套极有启发性的计算方式。以青竹村的实际情况,一年种早、晚两季稻子。一年下来,每亩地的生产成本包括种子、农药、化肥、雇佣耕种机、收割机费用等共计610元。一年每亩地需要30个劳动工,以现在农民打工每天收入60元来算,一年每亩地的人工成本为30×60=1800元。那么综合起来,一亩地需要生产成本610元加人工成本1800元,得出2410元的成本。以收益看,一亩地一年产稻900公斤,能卖出1350元。于是农民种每亩地的亏损为2410元与1350元的差额,即1060元。
在农民的种地成本中,卢国良以每亩1800元作为人工成本相当特别。虽然是在计算土地方面的收益,但是卢国良以农民打工的价格来衡量在土地上付出的劳动力价格。在2410元的总成本中,1800元劳动力成本占到近3/4。也就是说,农民如果选择种地,他的劳动力价值得不到相应的承认。
养猪、种果树或外出打工,农民也通过比较效益得出各家的结论。在养猪大村青竹村,养猪是最主要的农业收入。全村通过调查发现,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收入与养猪收入两项是全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而劳动力在城乡间的往来状况,与养猪收益成反向流动。
2002年和2006年猪肉行情低迷时候,形成了青竹村两个外出打工的高峰期。青竹村全村1557人,16~60周岁的男女劳动力有815人。其中,学校毕业到50岁以内的中青年劳力385人,卢国良以这385名中壮年劳动力作为调查对象。他发现,这部分人当中有25%的人是30岁以内有一定学历的,从中学或中专、大专毕业后,基本到沿海城市去打工,从事电子、通讯等行业里的技术工人。对于年轻人来说,主要是“价值观”使他们不愿继续留在农村,希望远离养猪种菜等农活。他们一年收入在1万~1.5万元之间,平均每年寄给家里5000~8000元。可见他们在城市中,生活并不富裕,属中下阶层。
在从学校毕业到50岁以内的中青年劳力385人中,有50%的人属于打工和务农兼顾的人群。他们在30岁到50岁之间,没有什么学历,已经在农村拖家带口,习惯于农业生产。为了使日子过得更好,他们基本选择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打临工。2003年,离村子仅仅两三公里,新建九华工业园区,需要大量劳动力。附近村庄30~50岁之间干建筑和装修的农民,白天在工地打工,晚上回家也可以兼顾一些农活,日子比较稳定。每年在外打工的收入在1万~1.1万元之间。
在城市边缘的九华工业园做更低级的收杂料、做木工的,则是村子里50岁以上的劳力,占到外出总劳力的10%。他们全职打工,并不兼顾农活。每年收入在1万~1.5万元之间。另外占到15%的外出劳力为女性打工,基本上在附近城市的纺织厂、槟榔加工厂工作。这些30岁到50岁之间的女性,并不兼顾家里的农活,每年务工收入在8000元左右。
2004年猪肉行情的高峰时期,青竹村外出打工人数最少,只有不到200人,仅为平时的一半。在养猪容易挣钱的年头,多数人选择回家干活而不去城市,只有30岁以下彻底希望抛弃农村的打工者才不会回家。
记者发现,近几年养猪这样的农副产品规模效应出现后,农村人口也出现分化。一部分靠养猪致富的大户,从养殖业里得到的收益已经远远大于进城打工,他们成为安心留在土地上的农业人口。以青竹村的莫石洪为例,500多头猪能为他一年带来30多万元的效益,四口之家无需外出打工来补贴。而其他30岁以下的年轻人,如果没有成为成功的养猪或种植户,宁愿一直在城市漂泊下去,等待着像李文斌一样,成为娴熟的城市工人,得到不错的回报。不少经济学家正在预测,随着中国工业化加速,“刘易斯拐点”是不是即将到来。虽然目前并没有确切的数据统计,但是随着实际上的农业人口减少,农业部门大量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判断,在基层的养猪大村也得到体现。
“猪荒”救急后的期待
青竹村属于湘潭市郊,与市区只有10公里的距离,不过由于村子处在响水乡的中部,除去人口变迁,城市化进程在村庄的外貌上还不是特别明显。位于107国道边的荷塘乡某些村子,已经大不一样了,一个个小型塑料厂、木材厂、水泥厂的招牌竖在道路两旁,农民们的房子尽可能集中在路边,干着些挖土扛砖的体力活。湘潭市岳塘区板塘乡的摇泉村已经被纳入了城市边缘,随着城市扩展,村子里水泥路边的房子紧凑地挤在一起,村民们人均只有两分耕地了。养猪在摇泉村占到农业收入60%~70%,村子紧挨着中央储备粮湘潭直属库,可以得到低价的玉米、麦麸等猪饲料。但是近几年工业企业发展非常迅速,37岁的肖建芳曾任板塘乡农办主任,现在是板塘乡政府企业办的工作人员,他掰指一算,板塘乡已有5个纺织厂、2家建材企业、7家砖厂,另加好几个炉具厂等。从2005年开始,肖建芳就明显感觉到这些企业的重劳动力特别缺乏,“农民的生活在提高,打工技能越来越好,很少人愿意干重体力活”。而不断扩大的企业生产线急需大批工人,致使数年前汹涌的民工潮,近两年变为短缺的民工荒了。湘潭钢铁厂前阵子到附近农村招工,每月1000多元的待遇,仍然招不够人。
湘潭处在丘陵地带,种田主要靠人力,很难大面积实行机械化。村子在不断变为城市,田地变成了水泥路,靠农业为生的人逐渐减少。
虽然湘潭的生猪产业化在全国已经领先,但所谓的产业化,与发达国家的方式相比,更多的还是“大散养”的格局。农民依然以一家一户的庭院式圈养为主,只是多数规模比以前大。肖建芳说,摇泉村2004年曾经设想过在村子里开辟一大片空地,真正把养猪业集中起来。但是城市化步伐太快,村子里的地也被纳入城市规划。湘潭市现在有各类养殖协会156个,一个成功的协会能够吸引几百家养猪户,在协会内部信息畅通。猪肉的产业链包括“饲料供应——良种供应——生猪养殖——生猪屠宰——猪肉分销——猪肉深加工”等环节,只是农户庭院式散户养殖依然是“小农经济”的传统。肖建芳有些感慨:“如果不是城市人吃不到低价肉了,基层农民的生活,很少有人会像这样来关注。”
经常到农村做防疫的湘潭市畜牧水产局总畜牧师吴买生感受到,多数农户渐渐对价格的波动有了自己的判断,即使今年行情再好,有些农民也只是摇摇头,“万一都开始养猪,过两年岂不是又跌得很惨?”在玉米、大豆都进入全球化、资本化的今天,小户式的生猪生产方式无疑受到严峻的挑战。去年“猪贱伤农”的经历,使吴买生和养猪户对今年的高行情也产生担心,“猪价并不是越高越好,今年是刚好赶上猪价自身的波动和去年疫情影响,高得不正常”。但是城市人口却一向认为,粮食和猪肉这些基本生活品,价格越低越能保障人民生活,这种想法让底层的农民很无奈。吴买生和卢国良在算账后都觉得,猪肉卖到10元一斤的行情,是目前“既能让农民获利,也能让城市人接受的价格,这种价格才能长期稳定”。
王伟筠是大连商品交易所信息部的副部长,自从最近猪肉行情飙升,大商所(大连商品交易所)推出生猪期货的设想就引起广泛关注。王伟筠说,其实大商所从2001年就开始对生猪期货的推出进行调研,在1995年粮油猛涨时候,很多人对刚刚推出的期货有误解,认为期货市场使物价进一步哄抬。“这就好像一个人自己长得难看,却怪罪于照出他面容的镜子。”现在一般人都认识到期货市场稳定价格体系的作用,稻谷、生猪与基本生活最接近的品种这些有可能进入期货市场,“期货市场将各种相关因素都装进了市场里边,市场加工出来的价格更全面,有预期性,它比一个单独养猪户的判断要可靠得多”。
当猪肉价格涨到十五六元一斤的时候,就在湘潭市畜牧水产局的新办公大楼里,任何与“猪”有关的人,都在团团转。8月初,湘潭市下属各区县的畜牧水产局负责人、兽医站的人都聚集起来开会,主管业务的副局长则在省里头接受最新指示。作为全国生猪主产地之一的湘潭,按照市畜牧站站长周炯光的说法,这里人均猪肉产量全国第一,但从未感觉“像今天这样受到重视”。农业部下派的工作组7月23、24、25日连续三天来到湘潭调查,每个县抽查30个典型养殖户,“光是每一户要填的表格,就有30多个”。7月26日,一份“赴湖南生猪生产督导组”的《湘潭市发展生猪生产的调查报告》就出来了。
与湖南类似,农业部7月底下派的20个工作组紧急来到全国各生猪主产区。7月26日,在长沙的湖南宾馆,农业部副部级总经济师和科技司司长带队的湖南工作组将湘潭、长沙、娄底三地的情况聚集在一起汇报。湖南省畜牧局水产局罗局长引用了两句话说明当前的形势,“无肉使人瘦”、“不可三日食无肉”,猪肉一向对多数中国人有着特殊意义。周炯光说,畜牧系统的人都知道一句话——“粮猪安天下”,老百姓吃不到猪肉与吃不到粮食一样难受。但是国家对粮食供应一直有特殊的保护政策,生猪市场在上世纪80年代完全放开后,除了中央储备肉基地等保障措施,基层养猪户的利益并没有纳入过国家的保障体系。
虽然形势紧张,拿着手里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吴买生和同事们都相当欣喜,因为文件“实在、特别容易操作”,有些措施正是7月底农业部调查后的结果。新措施让农民兴奋,“国家按每头50元的补贴标准,对饲养能繁殖母猪的养殖户(场)给予补贴”、“国家建立能繁母猪保险制度”、“国庆两节猪肉供应,猪肉主销区省、直辖市及沿海大中城市要将地方储备充实到不低于当地居民7天消费量”。吴买生与同事这几天正忙着到村子里统计母猪数量和人工授精的情况。只是他还有一点担心:“文件非常好,却没有说明这些政策执行到什么时候?”吴买生希望应急措施成为长期措施,“不然过两年猪价又像坐电梯一样往下掉,结果还是会猪贱伤农啊。”
责任编辑:乔春玲